
标题

标题
内容
七八九新军突起 | 塞壬
更新时间:2018-06-11 来源:广东文坛
塞壬:写作,与正在发生的同步

作家介绍
塞壬:原名黄红艳,湖北人,现居东莞长安。出版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三部。认为散文是最自由的文本,随时、随地开始,但永远不会结束。年少时,我在白色的石灰墙壁上用铅笔涂鸦的那些文字算是最初的手稿,那么大的墙面,我站着、蹲着,最后趴着。那是最初的写作姿态,散文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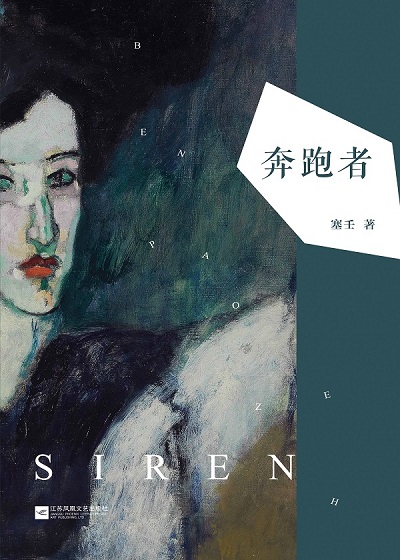
创作谈
散文漫谈
散文的容量
在很多人看来,散文这个文本是很雅的,借景抒情,人生感悟,小哲理,人生小趣味。行文讲究修辞,结构也简单,即使是回忆性的文字,也是娓娓道来,以情感动人,质朴真诚。这样的散文文本已经固化在我们的意识中,散文,书写着人类情感的那些美好的事物。
然而,散文是一种表达“我”的文本。既然是表达“我”,表达人,那么“我”除了真善美之外,也一定存在着恶与黑暗。甚至是,恶与黑暗更为真实。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是什么促使一个人一定要选择用文字表达自我?这个“我”到底想告诉这个世界什么呢?我们清楚,快乐可以是一个人表达的理由,那么,痛苦、愤怒它一样也是。生之为人,我们都不是来自于外星球,一个人的生活、情感都与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少数人拥有极为罕见、独特的人生经历之外,我们大部分人都过着同质化的生活,生活轨迹基本没有太多的出入。也就是说,表达我,就是表达这个世界,表达我的发现,我的不同,就是表达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就会清楚散文它一样承载着表达当下现实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表达中国人在当下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经验,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散文的容量是巨大的,这一点跟小说是相同的,它可以有宏大的叙事,它可以有惊涛骇浪,它可以有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书写,它有时间、空间的架构以及以情感得以推动的强大艺术感染力。它几乎是一个巨大的容器,承载人的方方面面,立体,富有层次,它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平面的,脸谱化的书写。在过去,也许很多人认为,当我在大街上见到一个性感美女而引起的生理反应,继而表现出失礼举动,这种细节是不可以出现在散文中的,在漫长的散文写作史中,我们看到太多的作品在选择性地表达作者自己的崇高,过滤那些真实的难以启齿的人性卑劣的部分,我们看到他们在散文中撒谎,遮蔽,矫饰。
生活更多的时候是充满悲伤。我们遭遇的现实,我们自己面对灵魂的异化,面对当下中国复杂的现实经验,如果选择书写,我们如何能够去绕开那些硌着我们的肉身和灵魂的巨大痛楚?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在文字中强颜欢笑,抒情?我们如何能屏蔽来自现实的场对我们精神的挤压与损害?我们如何穿越个人的精神地狱继而抵达澄明,如何在绝望中依旧相信爱,所有这些,都将是散文书写的大的母题,它映照宏阔的外部现实世界,指引人的内心抵达精神的高度。也许这样的写作进入的方式可能不雅,文字表达充满冒犯和入侵感,这样的书写可能披头散发,衣冠不整,面相狰狞,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表达,它直抵人的灵魂深处,反映真实的现实世界。这样的散文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成为了人,这个人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人。
有人说,散文的写作是个人的自传。不对,散文中的“我”应该是一个泛“我”,它书写的“我”可以是他者的经验,以我的视角来推进。在我看来,散文有浩瀚的容量,它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细水深流。对散文容量的拓展,是一个散文作家探索散文写作难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散文的真实与虚构
散文的真跟现实的真是一回事吗?散文书写的内容必须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吗?在很多的散文论坛中,大家都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最终也没有什么定论。但我始终认为,对散文的真实性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散文作家,而是读者。
对于散文写作而言,我向来不认为真与不真会是一个问题。一句话,我写散文从未考虑一个真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把真,当成散文一个难度,一个高度,当成好散文最重要的品质,甚至是散文好坏的重要标准。我就疑惑了,难道抄袭现实,复述发生的一个事件有那么难吗?难道大家不知道太多的粉饰太平、谄媚权贵的文章皆出于写作者的真心吗?真可以是好的,但是真,一样也可以是坏的。
我觉得真是散文最起码的标准,而且,假,也不一定就是坏的。这个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书写内容的真实,另一个是创作态度的真诚。什么是真呢?当我们面对现实世界,我们发现,这个真本身是复杂的,是浑浊的,它并非清澈如水,分分明明。因为它关乎着人的认知问题,面对白骨精变成的少女,孙悟空坚持说它是妖怪,而唐僧则坚信眼前的只是一位少女。最后观音菩萨给出了她的观点,她说,悟空看到的是真相,而唐僧看到的是人的心相。那么,这里面就很精准地阐述了不同的人,对真的认知也不同。那么,我们如何在散文写作中表现这个真呢?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想要的是真相还是心相。至于真诚,我认为写作的技巧可以左右写作的真诚,写作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演员的表演,如果你只能本色出演,那么你的写作注定窄化。在我看来,高技法的表演也是真诚创作态度的一部分。
我们对虚构的理解,大多认为是编造,是无中生有。实际上,如果作品的内在逻辑、审美、情感都符合我们基于对常识的判断,那么,即使它是虚构的,也不会有人质疑它的真。这样说来,真并不仅存于现实的真,对于写作者来说,真有可能存在于某种合情合理的虚构之中。没有虚构,一切写作都将失去想像的魅力,没有虚构,文字只是现实的尸体,没有虚构,任何写作将难以为继。当我们说,我认为,我想,这样的句式时,这里面已经在包含着篡改。
散文的真,不在写作者那里,相反,它在读者那里。只有读者才能认定作品的真与不真。也许,我很真诚地写出了让你觉得矫情做作的文章,也许我虚构了你认为很真的文章。画鬼,我们画出的也会是一个人的样子,变形的人的样子。再怎么胡编乱造,它还是会来源现实,有一种真,叫做,你觉得它真。
散文的难度
散文是一种内耗性极强的文本,它需要作家的情感投入,经验的储备,以及文化修养的底蕴都要有一种持久的续航能力。它要求作家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在中国,只写散文的人非常少,如果不在文本的边界上面寻找突破,如果不更新语言库,如果对文本的结构理解停留在旧式的模版中,不去在小说,戏剧,电影以及纪录片这类文本中寻求表达的新式语言,那么散文的写作是难以为继的。在我看来,散文的最大难度是在重新自我界定散文的边界。如果获得了全新的文本阐释,我认为,散文就会洞开一扇门。
表达我,除了表达视觉上、体验上的外部世界,除了表达我看,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我是什么。让人看你眼中的世界是容易的,但是把自己剖开给人看是困难的。在散文写作中,表现异质的自我,在日常中有精微的发现是难的。
我认为周晓枫对中国散文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提高了散文写作的难度。她的难度主要是表现在汉语的修辞上。她的语言有命名般的预言性,像是某种巫术和魔法,或者是炼金术,它唤起了是事物本身的灵性,在她那繁复、葳蕤而又充满神秘感的书写中,我们领略到汉语的精妙与深不可测的内在共谋特性。当她的散文成为一种标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制造了散文写作中语言的难度。我认为,语言的难度它实际上也是对发现的准确对应,归根结底,只有准确的语言才是最有难度的。文本、散文的边界,语言,容量,这些因素都是散文写作难度的重要节点,当然,散文写作会需要到写作者的勇气与真诚。这也是很难的品质。我认为,防止灵魂的干枯,才是一个散文作家最难逾越的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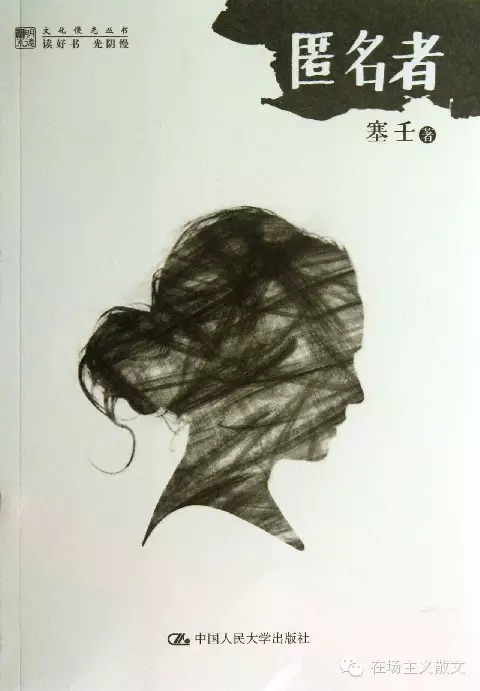
访谈
文学,情感上臻至一种自我陶醉
塞壬 & 中国作家网 周茉
在“面具”背后与世界对话
周茉:您于2013年出版的散文集命名为“匿名者”,您是如何理解“匿名者”的?为何将自己定位为“匿名者”?
塞壬:匿名者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存境况的选择。在广东,在生存的场里,我们很多时候是被时代,被某种特定的生存环境代号化了,比如进到一些公司,在内部你必须使用英文名字,有的是工作牌上面的那个编号,每个人对应的那就只有编码。此外,为了获得生存的空间,你有时不得不篡改自己的真实姓名与个人信息。匿名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但是,人活着除了生存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需求。当你匿名之后,你会发现,你忽然更开阔,更自由,你处在暗处,戴着面具,你会有某种窃喜与卑劣的快感,因为你的真实身份是无法进入那种环境的,类似于卧底。当你的匿名只是用来维持生存,那么那个真实的我,就会获得第二重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自己、他人。这不是对自我的质疑与逃避,相反,在这种角色的转换中,你可以看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更丰富的自己。
当记忆染上情感的气息
周茉:在一些关于湖北的散文中,诸如《悲迓》、《消失》、《1985年的洛丽塔》,您写城市化进程、写故土亲友、写自我成长,均脱离不了两个关键词:时间,变化。您的文字看似是在回忆中抒情,可否理解为亦是一种呼唤与对抗?
塞壬:我从来没有单纯地对抗过这些。对抗是一个相对没有退路与迂回的词,它斩钉截铁,它太简单了。我是一个情感无法一语中的的人。我的故乡,我的记忆,我的成长,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某种东西的消失,我面对它们的时候,情感是复杂的,荒谬的。我迷恋颓败,同时我为此悲凉,记忆之于消失,它既是痛苦也是欢欣,我的记忆随着我的不可救药的审美可以篡改,篡改成我迷恋的那个样子。我要说的是,文学,可以在情感上臻至一种自我陶醉,如果硬要说对抗,那一定是文学表达让它在那里对抗,达到表达的效果。
一座城,面朝未来,遥望故乡
周茉:故乡湖北给您留下的是深入骨血的“楚地悲迓”,它成就了您散文的一种属于个人经验的独特基调。若说它是原初的精神归宿,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第二故乡广东的呢?在您的文学之路上广东作为了一个怎样的存在?
塞壬:在《匿名者》散文集之前,我写了一本《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是这个集子的延续。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广东的流浪经历,下落不明的生活。没有广东的经历,我不可能写作,它不是影响我的写作,而是我的写作之源。只有在异乡才能眺望故乡,只有举目无亲,孤身一人,身心千疮百孔才能体会这人世之辛酸。我在广东触发了写作,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作家。
始终相信并保有爱的能力
周茉:您的几篇散文诸如《哭孩子》《羊》《托养所手记》,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生活中的混乱与疯狂,既是个体现象,又是社会中存在的真实问题,相信您辗转各个城市也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在进行这样的文字创作时您是否会有深深的无力感,甚至是对生活、对写作的终极目的产生怀疑?进而使这些题材的散文基调表现出些许沉郁与哀伤?
塞壬:我在创作这几篇文章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即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身在其中。我认为,即使自处内心的地狱,即使身处人生的低谷,也要满怀希望地相信明天,也要保持内心的鲜活与爱这个世界的能力,相信爱。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不会选择文字来表达。我几乎很少考虑终极目的,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我是一个深陷于内心与写作内部的人,极少跳出来思考遥远的,高深的,跟此刻生活无关的东西。沉郁和哀伤,我想是一个作家必备的特质。某种程度上说,因为沉郁与悲伤,才会发现身边一切细微而值得记录的美,才具备捕捉与体验这些情感的能力,才更能激发出爱的能力。
诉诸自我:情感的累积到释放
周茉:您在《文学无意识》中谈到写作仅是因为“写我所想”,并非有多么崇高的文学理想。那么对您来说散文写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塞壬:散文写作对我来说实现了自我的表达,对着这个世界表达了“我”。表达了我的发现,我的情感,我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我时常在不同时期去审视自己,我是否还是当初的那个我。或者说,我是不是呈现出了全新的品质与潜质。散文写作,我力图保证去写我必须写,我愿意去写的东西,这一点很难。每一次的写作,我几乎元气大伤,像大病初愈,散文写作过程是一个把骨血往外掏的过程,是一个精神内耗极重的一个过程。但,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后悔。
不改初衷的“纯粹”
周茉:您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第一本散文集名为《下落不明的生活》,记述了您所经历的状态,担任的工作,遇到的事,碰到的人。到第二本散文集《匿名者》出版,将近十年的时间,您对于散文写作的态度与认知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塞壬:这十年中,我收获了小小的声誉,生存状态得到了改善。但是,散文写作的态度与认知最好不要发生改变,最难的是,坚持初衷。尤其是在获得了一点点赞美与肯定之后更是如此。我当初写散文,根本没有想到文学、荣誉、功利以及写作以外的任何东西,坚持这份纯粹非常难,毕竟我也是一个俗物。我之所以还写散文,是因为我对表达自我,表达我看到的这个世界有着热情,我依然相信,在写作中,我可以摆脱一切困境,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要说实话,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维系表面的文学业绩的虚荣,我一直在写作散文。虽然有些情况下的写作初衷并非仅仅源于情感那么纯粹,但我依然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文字,每一次创作。
写作,与正在发生的一切同步
周茉:您的散文多以现实中的广东与记忆中的湖北为发生地,是相对遥远与动荡的岁月。现如今结束了那种不安的生活,相对归于平静。当越过了回忆的顶峰,当情感全部被释放,散文写作是否意味着迎来了一段时期的瓶颈?
塞壬:这是一个我回答得最多,也最不想重复的话题。安定的生活是有助于写作的,国内著名作家们皆是范例。散文的写作,回忆只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场,即刻的,当下的,正在发生的,身在其中的写作,显然,我属于后者。我的写作,将与一切正在发生的同步。情感是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东西,它不存在全部释放,只要不是灵魂干枯,情感是一个与生命同在的东西,生活在继续,个体参与其中,必然会有新的体验,会有新的情感。瓶颈这个东西是一个作家的常态,它需要一个作家的自我更新能力,续航能力以及新的经验的储备,好的作家能够很快作出调整。但我的瓶颈与我安定的生活无关。目前我已经开始了小说写作,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与自由,对于我来说充满着深深的魔力。我一直在尝试探索小说与散文的边界,试图找到两种文学形式过度的交点。
以文字书写传奇
周茉:最后,有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塞壬”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您为何要选取这个名字作为您的笔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塞壬:大家应该都知道塞壬的传说。但凡传说都让人充满了遐想。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传说,一个传奇。一个美貌的海妖,这个传说里有英雄,美女,死亡,色情,诱惑,以及某种神秘的力量,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吸引人的呢?我希望我的文字也具有这种魔力。我希望我这个人能够有妖的魅力,然后用一生书写自己的传奇。
创作年表
《一次次离开》发表于2007年《人民文学》第一期
《转身》发表于2008《人民文学》第一期;
《在镇里飞》发表于2008《人民文学》第三期;
《消失》发表于2009《人民文学》第四期;
《哭孩子》发表于2009《人民文学》第七期;
《匿名者》发表于2010《人民文学》第七期;
《托养所手记》发表于2011《人民文学》第十期;
《悲迓》发表于2013《人民文学》第二期;
《耻》发表于2014《十月》第四期;
《奔跑者》发表于2014《人民文学》第十二期;
《祖母即将死去》发表于2015《人民文学》第九期。
获奖情况
●2008年《转身》获第六届《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
●2009年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
●2011年《托养所手记》荣获第九届《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
●2014年散文集《匿名者》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提名奖;
●2015年散文《悲迓》荣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
●2017年散文集《匿名者》荣获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