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向卫国丨“随水而来”的物质想象或精神追踪
更新时间:2022-10-31 作者:向卫国来源:南方农村报
1
在西篱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昼的紫夜的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一段茂盛、药香浓郁的野菊花,像在列队欢迎她。她想为它们歌唱,没来得及发声,疼痛就像雷电一样快捷,令她支撑不了自己,倒下,在野菊花丛中,下午四点整,生下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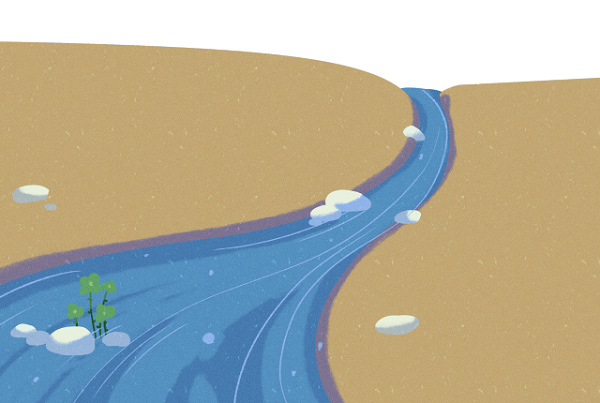
生命就是一趟随水而来,又随水而去的旅程。
小说的自传性及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会让人自然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诗人西篱,或者至少是西篱想象之中的另一个更本原性的“西篱”。
作为读者,在我看来,这一段文字同时提供了西篱诗歌中两个原型性质的物质元素或物质想象——水和植物(花)——的原始性来源。因此,西篱最近的诗集名曰《随水而来》,诗集中乃至她全部诗歌中最重要的诗作也是长诗《随水而来》。
2
西篱名字为其父所赐,得于陶诗“采菊东篱下”的另一版本“采菊西篱下”。她16岁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美丽的花溪滋养了她的生命,同时激发了她最初的诗情。她在《怀念花溪》里吟唱——
四月金黄的花海
就在溪畔生长
直长到贴近蓝色的天空
爱梦的女孩
就在花蕊的中央做梦大学阶段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生命的重要驿站,它是除童年之外,滋养生命和梦想成长的另一个浪漫和幻想之域,自此以后,社会将会给予人生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多年之后,当诗人再次回忆花溪,“花”与“溪”仍然是最重要的梦想元素,由它们所滋育的情感亦再次化育为诗歌和爱情:
我想知道
还有没有另外的人
和我一样
在这美丽的水边成长
如果是五月
绵绵细雨就会涨满她的心房
涨满她恋爱的愿望
西篱大学毕业之后,在文学月刊《花溪》作为文学编辑工作了一些年,但最终她离开了,去到更遥远的南方羊城定居。“随水而来”是从旅途的终点来看,如果从起点看,就是“随水而去”:“我知道/即使寒冬降临 大雪纷飞/花溪也依然碧绿/运载着朵朵雪花/流向远方……”
可以说是花溪的水把她载向远方,但更为本质的,是一种如烟雨一般朦胧的梦想,带走了她。流水和烟雨,始终如一种情绪的云雾,盘绕在她的诗歌中,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过。
3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随水而来”的动态形象,决不是一个随便的命名,它既是个体也是一个生命的集体原型或者关乎生命来源的隐喻。
随水而来
它无声无息却长驱直入
在它汹涌之峰的上部
日光闪烁的地方
生活
正消融其实有的一切
——《随水而来》
当现实中的一切随着时间和个人生命的悟入而逐渐“消融”,失去它的实有性,反转为虚幻的梦境时,生命又再次听到甚至是看到那流水,那承送着生命来去的最初的水。于西篱而言,水不仅是送来生命的使者,也是运送生命去往远方的航船,人的一生逐水而来,跨水而去,最后又回到原始的水和植物。
噢 水们漫过街道
然后毫无动静
石头爆裂的声音
将在明天响起
无论如何
我也得跨过这水……
——《水》
让人疑惑的是,西篱有写给父亲的诗《父亲》,而母亲的形象在她的诗歌中基本是缺席的,只偶尔会泛指性地出现“母亲”这个词。西篱的传记小说《昼的紫夜的白》讲述的就是一个“寻找母亲”的故事:“我”的母亲在生下我后不久音讯杳无,成为一个理论上永恒的失踪者。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是一种想象和意念,并不能转化成具体的诗歌实体意象。在这个意义上讲,母亲和“随水而去”的“水”一样,都是无法完成塑形的深层物质或元素。
4
在西篱的诗歌中,反复出现过以植物(尤其是花)自喻的诗句。也就是说,植物或花在西篱诗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情感对象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因素而存在,而是更为内在和深刻的生命元素,或将生命幻化的欲望对象。这或许因为从元素性的“水”中诞生出来的最原始生命形象就是植物(微生物虽然是更早的生命,但它不在人的视觉范围之内,无法成为生命感知的对象,从而也自古就缺席于心理、艺术的意象世界)。从诗人在自传小说的虚拟和想象中,将“自我”诞生于花丛(也许本来就是真实的写照),以及在“乡下”的大自然中最初的成长经历,到花溪两岸四季数不清的花朵对诗人的视觉、嗅觉和情感梦境的长年浸润,不同时期带有共性的知觉想象因素,使得诗人几乎终身都有一种将自我的生命植物化的冲动,或许这原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将一切主体都进行自然化处理的倾向在现代诗歌中的隐性存在。
把自己看作翠绿的植物
我们来自乡间 那时十六岁
——《温柔的沉默》
他关注的孩子
是雨水一样的花朵
谷粒一样宁静
——《温柔的沉默》
望那我们想的地方
像两朵花一样
——《梦歌》
我们双双躺着
像两朵小小的浅浅的花
——《梦歌》
而我,是屋子里的某一角
一株淡金色的植物
——《屋子里再不会有人来了》
除了作为一朵花
一株自然的植物
你又还是什么呢?
——《随水而来》
上述类似诗句的反复出现,有如某些基本的梦境,常常伴随某个人的一生,它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一个诗人对“自我”的沉浸和对自我生命来历的追问,有时比哲学家更为迫切和显得更为生命攸关。而母亲实体形象的缺失,这种非常特殊的个体生命遭遇或命运,或许也会导致人在找寻自我生命来源的时候,在潜意识或者不自觉的幻像生成中,以自我认同或热爱的另外的形象,暗中实施了生命的物质元素和生命诞生的场景置换。
5
水和植物,这两种物质形象的另一个无意识的衍生形象,是语言和诗句本身。从词语到诗句的生长、流动,直到最终成为一首完整的诗的过程,也十分类似于或完全可以类比于在水的滋养下,一株植物从发芽、伸展出枝叶,到最后长成植株的过程。我们有理由认为,诗人对此是有一定的意识觉醒甚至自觉认知的。
让我们再次回到花溪:
我在十月南方的人流之中
抬头看见天边的花溪
那风和阳光的声音将诗歌吟唱
心灵在清澈之中开始激荡
——《怀念花溪》
在那诗人幻想的“天边的花溪”,诗句被“风和阳光的声音”自然地吟唱出来,显然这诗就像花溪的水和花一样,是大自然本身的产品。因此,水和植物的物质形象,不仅是个体生命所希望的幻化对象,在诗人的想象中,也是诗歌和诗句的语言形象之隐秘的或心理上的物质前身。
更为深入而具有多种综合意向的诗句是下面的这一段,诗人显然是将主体的水、植物、“我”和语词构成的诗句等四种物质形象,同时幻化为一了:
即使明天的我
只是些如水的诗行
对奇迹永远的追逐
已在生命里布满了辉煌
我生长在那一片金色之中
那秋日的净土安宁而芬芳
——《我守在那一片金色之中》
在这一段诗中,“植物”元素,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那一片“辉煌”的“金色”显然就是诗人多次自喻的植物形象。至于为什么诗人渴望成为的植物,都是“金色”或“淡金色”,必然会再次让我们想起她诞生于金色的野菊花时那个生命的伟大场景;存在于诗人深层意识中的那个“金发的婴儿”(《雨的夜歌》),必定是披散着金色花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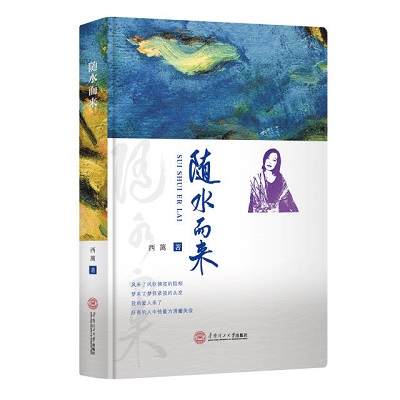
《随水而来》,西篱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